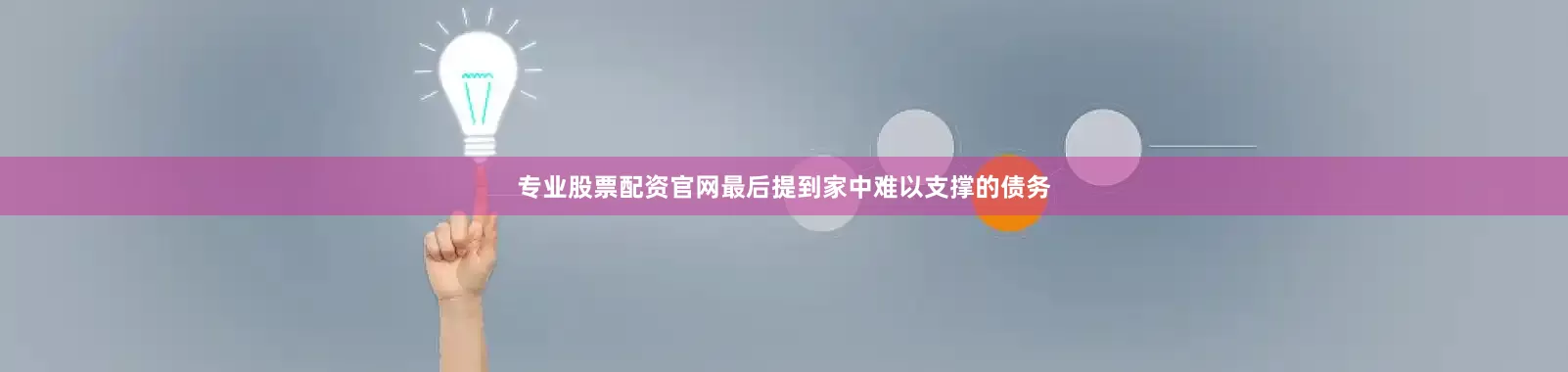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裴思童

2024年1月10日下午,我坐在床边,打开了一本翻旧的、蓝底硬壳的《水浒传》。这是我的上一位采访对象送给我的,他叮嘱我,一定要一个月后再打开。
在遵守诺言等待的一月内,我数次想过这本书里会有什么。书签?画作?又或是一封信?为什么要一个月后才能打开?
抱着好奇,我翻开那本书,没等我反应过来,几张皱巴巴的百元大钞便从书页中跳出来,我震惊地往后翻,几乎每隔几十页,书里便夹着几张百元现金,加起来,共有2000块钱。
这让我很惊讶,这是我第一次遇到采访对象给我塞钱,更何况这是一个生长于云南大山,患有抑郁症,年仅15岁的彝族少年。
2023年年尾,我在社交媒体上第一次看到他。那时他因独自一人从云南临沧骑行到昆明而被人关注,镜头里,这个男孩看起来局促、瘦弱,他聊起自己的抑郁症,谈起学业和父母的压力,最后提到家中难以支撑的债务,流下泪来。
这个画面搭配视频下方那个颇具噱头的标题——“15岁学霸少年重度抑郁休学骑行自救”——让人忍不住想象这位少年背后的故事,以及背后所折射出的更公共性的问题。
抱着这种探寻,我飞往云南,和他一起待了5天。结束时,我在返程的飞机上心情沉重,思考我还能为这位少年提供怎样的帮助,从没想过我会在一月后收到他留给我的2000块钱。
我知道他收到了一些捐助,但我始终记得我在他家中看到的画面:可以称之为家徒四壁,几间破落的房子看起来随时可能塌下来,除电灯外几乎找不到什么电器,我在透风的房子里合衣睡了一晚,第二天便发了烧。
他为什么要给我这么大一笔钱?我第一时间将钱转了回去,然后打电话“质问”。电话里,他给了一个我没想过的答案,他说是因为他曾听我谈起我的压力和困境,担心这趟遥远的采访给我带来额外的经济负担。而之所以要我一个月后再打开,是因为他估摸这时候稿件应该已经发出来了,怕我误认为是他想要就稿件内容“贿赂”我。
“首先,出差的费用报社会报销;其次,我也并不缺这笔钱。”我有点哭笑不得地回复。然后开始回忆,是什么让他产生如此误解。翻阅采访记录,我找到一个画面。那是采访的第三天,在滇池边,我和他蹲在石头上,有过一小段争执。
那时我十分焦虑,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独立出差,但在过去三天,采访进度一直停滞不前。在昆明,他身边围了一圈想要拍摄他的骑行客,我很难在这群人中找到与他单独相处的空间,而仅有的碎片时间里,他又一直在重复那些我听过很多遍的老套叙事,听起来和任何一个困于学业压力,认为父母不理解自己的青少年没有太大不同。
在嘈杂的昆明,我觉得我很难理解他真实的困境与底色,而他对于家庭和父母单方面的讲述,也让我有所质疑。
为了让采访更进一步,我谨慎表示,如果有可能,我希望能够回到他的来处,见见他的父母。如我所料,他表现出明显抗拒。过去三天建立的信任似乎被他一瞬收回,他指控我:“我以为你理解我,但我现在觉得你只是为了完成你的工作。”
他可能说中了一部分,但我又觉得他所指并非全部。或许为了自证,或许为了挽回信任,我向他聊起自己,那些曾和他相似的困境,半是技巧,半是真心。不知什么打动了他,总之最后,他向我卸下防备,并意料之外地答应我,带我回了家。
从采访来看,这是成功的决定。当我早上6点从昆明出发,一路转高铁、出租车、大巴和皮卡,在晚上10点到达他家,站在那个放眼除了山什么都看不见的院子里,听他讲他从小到大的生活,和他沉默、辛劳却也传统、威严的父亲坐在一起,听着他母亲的哭声时,我抛下所有公共性的议题,无比具体地看到了这一个少年的困境。
在澜沧江畔,颠簸的老式大巴车上,他靠在我肩头睡去。我看着蜿蜒地像看不见尽头的盘山路,想起他宏大的梦想和他世代没走出过大山的祖辈,忍不住流泪,我想我理解了他为什么想要逃离。
但他塞给我的两千块钱又让我想起他对我的质问:“我是真的在理解他,还是只是为了完成我的工作?”这趟归程的确帮我完成了采访,但对这个为了逃离家庭独自骑行一千多公里的少年而言,我拉他回去又有什么意义?
我曾经欺骗自己有意义,因为他告诉我,我可以帮他与父母沟通。但后来我知道,他真正的理由其实是,担心我这么远跑来,如果没有办法很好完成采访,可能难以和领导交代。
做记者两年多,我见过五花八门的受访者,这一次,我用职业性的技巧不小心交换到了一点少年的真心,这让我不安和惭愧。
我曾经听一个很有名的记者谈到,做记者有时很残忍的事情是,当受访者跟你袒露最脆弱一面的时刻,记者的心里总难免夹杂一点兴奋,因为你知道,你迎来了采访中的“Golden Moment”。
我曾在采访中遇到过很多个这样的“Golden Moment”。比如山火过后,宣传部门带着护林员向我回忆队友如何在他们眼前逝去;也曾想办法找到被继母施虐的孩子的生母,问询她是否了解孩子的情况。这些时刻通常让我难过和痛苦,但这份沉重的尾调又免不了有一声轻松的叹息:“采访终于有了突破。”
这或许是作为记者,一个职业性与人性交织、难免共存的矛盾。这并非什么新鲜的讨论,只是时常会被遗忘。我想少年给我的两千块钱,就在提醒我:当高举新闻公共价值的外壳时,不要忘记看见笔下具体的个体;当感到采访有所突破的瞬间,不要忘记警惕心里那声轻轻的叹息。
来源:中国青年报客户端
股票办理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